好姐妹临死前,让我嫁给她老公
北塘新区刚打地基那会,程莹就拉着老玉去看了好几回,机器的轰鸣声里,程莹扯着老玉的耳根子讲:“老玉,盼了多少年,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都不敢想啊!”
老玉腿脚不利索,往前挪一步眯眼感叹:“到时候咱好好和政府讲一下,争取要个一楼。”
程莹拢了拢鬓边的白发,笑着接应:“行,还是老规矩,你说了算。”
日子打指缝间漫过,高楼拔地而起,程莹一天跑三回,眼巴巴盼着。
老玉虽说腿脚不便,仍是闲不住,捡破烂当成了事业,干得悠哉乐哉!
一转眼,就是来年春天。
北塘新区的住宅楼交工加装修几乎是一气呵成。
北塘棚户区开始陆续搬迁,老院子逼仄,一颗老杏树周身用板子搭了个窝棚,算是杂物间,东西搬空了,杂物间一拆,老杏树显出了原来的样子,风一吹,花苞散了淡淡的香气。
程莹鼻子一酸,心头不是滋味。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在这个憋屈的地方没住够是咋地?眼下有了新房子,你还抹上泪了,快些吧,别家都搬完了。”老玉还是急脾气。
“再憋屈也住了三十多年了,到底是自己个的家呀!这将来拆了,这老杏树能保住吗?”程莹依依不舍地念叨,心底里舍不下一个人。
“你管它干嘛!麻利走喽!”老玉八十多岁的人了,脚蹬三轮车一跨呼呼生风,威风不减当年。
程莹护着老院子里的破铜烂铁,宝贝似的,一路向着新房子进发。
棚户区的老邻居前拥后挤,小区里叽叽喳喳热闹得像过年,棚户区憋屈久了,赶着政府的好政策也亮亮堂堂过几天舒心日子。
程莹一只脚才迈进门,就激动地喊:“老玉,快来看,阳台真大,我得多养点花,我就稀罕花,哎呀,你看看,这卫生间,瓷砖真漂亮。”絮絮叨叨没个停。
老玉瞪车累了,点了一支烟鼻子一哼:“没出息呀,刚才你还在那屁股都转不开的地方抹那二两猫尿呢!”
“哎呀,老玉,新房子不能抽烟的。”老玉咧嘴一笑,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脚一拧,程莹心疼地大呼:“哎呦,我的地砖。”
呼喊间,两个人忙跌跌去擦地。
新家安置好了,为了庆贺新房子乔迁,老玉在本地的四个儿女都来了,晚上吃的是火锅。
照例是程莹在厨房里忙活,洗菜、摘菜、调配锅底,准备的一应俱全。
饭间,远在美国的老大打电话过来祝贺,一家人其乐融融,程莹挨着老玉坐,儿女们也算是孝顺,举杯齐声祝福:“祝愿老爸和程姨搬进新家,安度晚年。”
老玉颤抖着手举杯哽咽道:“哎,好日子来了,就差朝霞看不见了。”
朝霞是老玉的前妻,死于肝癌。
好好一顿饭,吃得悲喜参杂。
晚间,儿女们都散了,老两口舍不得睡,开着灯唠了大半夜。
第二天,老玉就出事了。
起因是老玉闲不住,非要出去捡破烂,回来舍不得往沙发上坐,准备洗个澡,结果前天晚上没睡好,水龙头刚打开,程莹就听见“扑通”一声,接着听见老玉“哎呀”喊了一嗓子,再没了声息。
120打得及时,人送到医院总算是脱离了危险,儿女们七嘴八舌地嚷嚷,大意是怪程莹,他们一致认为是程莹嫌弃老玉捡破烂脏,才出的事。
程莹一肚子委屈,浑身有嘴说不清。
尤其是老玉那小女儿,说话更难听:“程姨,当初您在棚户区住,也没见过您多讲究,怎么住了一天新房子就嫌弃我爸了,我爸捡破烂那钱不脏啊?!”
程莹顿了顿说:“小萧,你就是在棚户区长大的,这话说不得啊!”
“怎么了?程姨,那我还……”小萧话说了半截,老玉醒了。
一家人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
晚间,程莹打发走几个儿女,自己留下来陪着老玉,她趁老玉睡着的时候小声讲:“老玉啊,你可千万快些好起来,咱这好日子才开了头,一辈子了,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在那棚户区,好不容易政策好了,政府给咱们建了新楼房,咱们得好好地享受,你说是不?朝霞姐也盼着呢,我前几日,就怕我等不到那楼装修,我怕朝霞姐住不上,你得好起来,叫她看见咱过上了好日子。”
冷不丁,老玉伸出大手握住了程莹的手。
程莹流着泪破涕为笑,心里的委屈也散去了大半。
本来老玉眼见着一天天好起来了,谁曾想,三天后,人突然就陷入了重度昏迷,
被送进了ICU。
ICU那是生死门,只要进去了,便是生死难料,更何况,老玉八十多岁的人了,虽说平时身体健朗,没病没灾的,可到底是摔了一跤,一切都不好说。
小萧的话越发难听了:“程姨,想不到你居心叵测啊!为了一套房子,这是把老头往死里整啊?”
程莹无心与他们扯皮,她心里直打鼓,万一老玉出不来,她就剩下孤苦无依了。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她就真的孤苦无依了。
老玉住进ICU三天后,程莹实在熬不住了,她打算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再回来照顾老玉。
钥匙插不进去,她找了半天,没有钥匙孔,她明明记得刚搬进来时,钥匙很容易就插进去了。
她急得满头大汗,门还是打不开。
物业的过来一看,笑着说:“大娘,您这已经换了密码锁,得用指纹或是密码,估计是孩子们担心您的安全,给您换了新锁,还没来得及告诉您,您打电话问问密码就能打开了。”
程莹给老玉的二儿子打电话,电话那头阴阳怪气地讲:“程姨,那房子是我爸的,如今我爸住进了ICU,生死不定,您再住那房子不合适了吧。”说完挂了电话。
程莹一屁股坐在楼道里,她惊天动地的嚎了一嗓子,多少年的委屈都没有眼下这把密码锁扎心,她辛苦操劳了半辈子,为老玉,为这个家,甚至是为那死去的朝霞。
可眼下,老玉还没死,孩子们就这样对她。
邻居们听见动静,都跑过来安慰程莹,说等老玉醒过来就好了。
程莹抹干净眼泪,直奔医院。
ICU里,老玉依然躺着,无声无息,程莹实在太疲累了,她在走廊的椅子上对付着,就迷糊着了。
北塘棚户区那些糟心的岁月,程莹想想都觉得难捱,可到底是嫁给了自己可心的人,再难熬她也愿意。
五十年前,她第一次走进北塘,眼前是一条条纵横交错歪七八扭窄细的巷子,春天风一吹,尘土飞扬,遇上雨天坑坑洼洼无法下脚,冬天一到,巷子口倒的都是泔水,下场雪一踩,早晚一冻,不当心就是一跤,摔个人仰马翻。
最要命的是旱厕,一大早十几个人等着排队,遇上个跑肚拉稀,简直能要了命。
老玉在钢铁厂做工人,一大家子挤在不足四十平米的房子里,院子逼仄的比不上农村的猪圈大。
程莹就住在老玉家隔壁,那时候老玉的老婆还活着,家里七大八小五个孩子,每天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程莹是偷跑出来的,家里的男人喝醉酒往死里打她,怀孕六个月,男人还照样打她,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偷跑出来。
也没想着活,可人拗不过天,是老玉救了她。
老玉是钢铁厂的轧钢工人,程莹沿路乞讨,一路进了城,钢厂就在城郊,程莹半夜没地方去,倒在钢厂的大门口,遇上了下夜班回家的老玉。
他把她背回家,老玉的老婆叫汪朝霞,是个热心肠,一口米汤一口面汤地伺候她,程莹活过来了,她跪下说:“感谢大哥大嫂,俺这辈子当牛作马报答大哥大嫂的恩情。”
朝霞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说:“大妹子,你可别,你这不是把俺和你大哥说成是剥削阶级了吗?”说完,她又接着说:“以后别叫嫂子,叫姐,好好养身子,把孩子生下来,有大哥和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和孩子。”
那时候,朝霞在纺织厂做女工,任务来了,忙起来四脚朝天,程莹拖着临产的身子一边帮着照顾几个孩子一边不误做些零碎活,老玉和朝霞虽说待她好,可她也不能吃白食。
孩子临近出生的半个月前后,老玉天天上晚班,朝霞厂子里也忙,程莹到底是出事了。
男人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程莹住在城郊钢厂的棚户区,探摸了几个晚上,找来了。
拳打脚踢逼着让程莹回去,程莹死活不走,生拉硬拽间程莹摔倒了,身下殷殷的血迹蜿蜒流淌,程莹和男人撕扯哭喊间,朝霞回来了,她一看,程莹身下一滩血,男人还扯着程莹的衣领暴凶,吓出一身冷汗:“大俊,快去找你爸。”
大俊是老玉的大儿子。
朝霞顾不得许多,她从屋里抽了菜刀,朝着男人劈下去,男人原来是个怂蛋,看见朝霞手里的菜刀,放开了程莹,软塌塌退了三步,朝霞护住程莹扬着嗓子骂:“混蛋,赶紧滚,程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娘饶不了你。”
男人屁滚尿流骂骂咧咧:“城里的婆娘都他妈是泼妇。”一溜烟没了踪影。
老玉回来了,背着程莹雇了巷子口的脚踏三轮车奔去医院,命悬一线的一夜,朝霞守在程莹身边,老玉蹲在走廊里抽烟,生死攸关,大人总算是保住了,孩子自然是没了,更惨的是,程莹子宫受损,再也不能生育了。
程莹醒过来问:“朝霞姐,非亲非故,为啥舍命救俺?”
朝霞哭了,她说:“俺有个妹妹,这里有些毛病。”
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门,接着又说:“就是神经病,一犯病就疯疯癫癫没个人样,其实她从前好着呢,就因为男人做了乡干部,变心娶了黄花大姑娘,她受了刺激,就疯了。”
“再后来,人跑出去落水死了,那夜,老玉把你背回来,俺一看,你身子那么重,但凡好过点,这年头吃食紧巴巴的,哪个愿意往外乱跑,俺就不由得想起俺那妹子,就当是她回来了。”
程莹知道自己的孩子没了,可她不愿意再给救她的人添堵,她把苦都咽了下去。
朝霞是聪明人,她一把拉过大俊说:“大俊,你记着,这是你姨,也是你妈,你就是她儿子了,将来不管遇着啥情况,你都得管她。”
大俊那年十三岁,摸摸头憨憨一笑,闷声闷气喊了声:“姨妈。”
朝霞噗呲笑了。
程莹别过脸,满心的凄惶。
在老玉和朝霞的帮助下,程莹经过千难万阻,把婚离了。
朝霞把院子里的一间小厢房收拾出来,程莹就算有了家。
好日子过不到几年,赶上了下岗的大潮。
朝霞的纺织厂效益不好,她成了第一批下岗工人。
愁云惨淡的光景也没把朝霞难倒,她摸了一把淌出眼角的泪说:“下岗是个啥?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两个月后,朝霞在巷子口开了一家棉布店,叫霞莹棉布坊。
老玉打趣:“就这灰头土脸的两间小土屋,还棉布坊,你不是要逗死街坊邻居吧。”
朝霞不气不闹,她接着话茬讲:“老玉,你不信,俺能让这棉布变出新花样,是吧,程莹。”程莹笑着看他们夫妻两个逗趣。
她想,朝霞真是个有福气的女人,遇到老玉这样的好男人,知冷知热,说话从来都是逗逗趣趣的,不像她老家的男人,对自己老婆喊天震地的,一天天没个好脸,她自己就更不用说了,命比黄连还苦,遇上个四六不开的铁渣渣。
在朝霞雷厉风行的行动下,棉布坊开业了。
门前是黄土大路,下午小商小贩云集在此,卖些个时令蔬菜瓜果,也有近郊的农民在农闲时抱着鸡呀鸭呀的来卖,夏天暑热的时候,钢厂会给放上几场免费电影。
每到那时候,人山人海挤挤攘攘,日子久了,竟也慢慢形成了一个农贸集市,虽说是在土滩里,可也是一片热热闹闹的烟火光景。
朝霞心灵手巧,从纺织厂低价进棉布,置办了两台缝纫机,开始了简单的棉布加工。
她悉心教授程莹蹬缝纫机,起初程莹不肯学,她说害怕脚蹬踏板不利索,针头扎了手,朝霞笑得前仰后合,她说:“程莹,你去看看厂里的机器,你不得吓得尿了裤子。”
笑够了她接着说:“你得学,人活着,手里得有吃饭的家伙,这眼下蹬缝纫机就是咱吃饭的家伙,学到手了就是饭碗,一点不比公家的差。”
程莹在朝霞的鼓励下,壮着胆子学,她不知道,她天生就是蹬缝纫机的料,连朝霞都说:“哎呀,看看,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你这怕是要饿死师父了。”说完两个人闷头大笑。
在小店里,朝霞负责裁剪,程莹负责机工。
她们主要做的就是床单被罩枕套,有时候加工一些窗帘,为了多出新花样,朝霞还特意花钱去了省城,学习新式手艺。
程莹被朝霞的劲头感染着,她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她能在城里自己挣下养活自己的钱。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她和朝霞也越来越忙,有时候,遇上个结婚嫁娶的,四铺四盖的订单,两个人连夜赶着做,做累了在店里支个小锅,下面放点固体酒精块,白水煮挂面,吃得满头大汗,程莹说:“朝霞姐,你要是俺亲姐该多好。”
“俺就是你亲姐呀!”朝霞笑着说,她喜欢笑,笑着用筷子敲程莹的脑袋。
程莹满眼热泪,和着热气腾腾的面汤咽下去,日子过得展了些许眉眼。
朝霞和老玉的第六个孩子出生后,朝霞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她经常吐槽说:“哎呀,这孩子生多了,就是容易老,我最近老是乏力,感觉老犯困。”
程莹知道,她不是生孩子犯困,她是太累了,六个孩子,又要上学又要吃饭,尤其前面两个大男孩,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可累归累,乏归乏,朝霞照样铆足劲干,生意越来越好,店面需要扩张,朝霞和程莹就合计换个大一点的店面。
却不想,店面还没看好,朝霞就出事了。
临着中秋节,钢厂效益好,老玉发了福利,大袋的西瓜和苹果。
朝霞和程莹干了一天活,累兮兮的,孩子们吃够了。
朝霞也分吃了一块西瓜半个苹果,平时这些她是舍不得沾一口,结果半夜就开始吐,小腹跟着隐隐疼,朝霞以为是胃痛,吃了两片胃药,似乎缓解了好多。
接下来隔三差五的痛,她虽说感到乏力,也是咬牙硬撑着。
眼见着人一天天消瘦,饭量越来越少,是程莹先发现的,她说:“姐,你眼睛怎么一天比一天黄了。”
“人老珠黄呗!”朝霞自嘲道,说完哈哈大笑。
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朝霞半夜腹痛惊醒,老玉是大夜班,屋子里冷飕飕,朝霞肚子越来越疼,她不敢惊动程莹和孩子们。
自己坚持着绞了热毛巾,额头的汗越来越多,她实在疼得不能,就死死咬着毛巾,可一点气力也使不上,人几乎要疼到虚脱了。
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撑着最后一口气喊:“大俊,大俊。”大俊闻声起来,看见母亲佝偻着身子匍匐在被子里,嘴里死死咬着毛巾,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
他冲出门喊:“程姨,程姨。”接着跑出去借三轮车。
程莹再不似当年那般羸弱,她冷静地指挥着二海看好弟弟妹妹们,自己背起朝霞就走,朝霞大概瘦了很多,或许是程莹心急如焚,她一路小跑,出了巷口,寒白的一片天地,没有一个人影。
朝霞在她背上疼得呜呜咽咽呻吟,程莹顾不得其他,继续背着朝霞跑,迎面一个黑影,是大俊,三轮车借到了。
一通检查做下来,医生办公室,刚刚从车间奔回来的老玉气还未喘匀,就听见医生说:“肝癌晚期,做手术也没有多少意义,先办住院手续保守治疗吧。”
老玉愣愣怔怔,半天没反应过来。
程莹吓傻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迈不开,忽地,她像发了疯一样扑上前扯着医生哭喊:“大夫,不可能,她就是胃痛,你们一定是检查错了,不可能。”
大夫无力地摇了摇头。
程莹依然不撒手,她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姐,你重新检查一遍,肯定是弄错了,你们不能这样。”
几个护士涌进来,她们极力安抚着情绪崩塌的程莹,但程莹像头发疯的母牛一样,哭嚎呐喊,四处冲撞,死死嵌着医生的大腿不肯松手,老玉一把扯起程莹艰难地说:“不要闹了,朝霞听见不好。”
程莹这才意识到,她可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她赶紧收了眼泪,爬起来跟着老玉昏昏沉沉离开医生办公室。
诊断书没敢给朝霞看,出了办公室,老玉蹲在医院的角落里,抱着头呜呜咽咽地哭,程莹站在老玉身旁,脑袋嗡嗡响,她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大男人为了老婆哭得那么无助而伤心,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
但那一刻,她一点泪也流不出,她还存着侥幸,也许真的是弄错了。
老玉担心朝霞起疑心,嘱咐好程莹说辞,擦干泪回病房,老玉和朝霞说:“哎哟,一点小病,还非得让住院,不过一个胆结石,还非说是要手术,你估计要忍几天了。”他说得轻描淡写,却始终不敢抬头看朝霞的眼睛。
朝霞何其聪明,她假装生气:“老玉,你抠门啊!”
程莹在一旁,只觉得天旋地转的难受。
老玉去办住院手续,朝霞拉着程莹的手说:“程莹,听姐的话,回家吧,这病烧钱也续不了命,家里没多少钱,姐不想为了这没指望的病欠一屁股债,不能叫孩子们一辈子住在棚户区。”
“姐,大哥说了,就是胆结石,做了就没事了。”程莹极力糊弄着。
“姐都听见了,肝癌晚期,三个月了,咱回家,你好好给姐做点好吃的,也让姐享享你的福,算姐没白疼你一回。”
她说得风轻云淡,一边说一边笑,程莹实在忍不住,那一刻,她才确信朝霞是真的得了绝症。
她想抱着朝霞哭,可又不敢,只好继续哄:“姐,你不要说胡话,哪个还往自己身上揽病啊!”
说话间,老玉进来了。
程莹看了一眼老玉,还没等老玉说话,朝霞先说:“老玉,回家。”
“回什么家?明儿个手术,住院手续都办好了。”老玉装作笑眯眯的晃了晃手里的单子。
“你办什么住院手续?大夫都已经说了,保守治疗,这就等于是白花钱,我们有多少钱在这里耗啊?!”那是朝霞第一次冲着老玉大吼。
老玉怔怔地望着朝霞,他手里的单子抖落在地,他知道终究是没瞒住,他上前抱着朝霞说:“老婆,不是你想的那样。”
朝霞闭眼咽下了涌上来的眼泪,她捶着老玉的脊背哽咽道:“老玉,让我回家吧。”
老玉拗不过朝霞,住院手续办退,朝霞到底还是回了家。
头几天还好,朝霞虽说精气神减了,但骨头还强撑着,她有时候怕老玉和程莹看出来,当着他们的面笑得乐呵呵,好像她天生不怕死一样,可死谁不怕,背着他们朝霞哭得肝肠寸断,她舍不下老玉,舍不下孩子们,也舍不下程莹。
可舍不下又能咋样?人拗不过天。
朝霞越是这样,老玉和程莹心里越是憋屈,好好一个人,䞍等着熬得油尽灯枯,活活等死。
腹痛越来越严重,任朝霞再钢的骨头也撑不住了,她起先抱着老玉的胳膊,疼得厉害,手指掐进老玉的肉里,老玉抱着朝霞,两个人像是被搁浅上岸的两尾鱼,忍着挣扎着,体会彼此的伤痛。
锥心的疼痛夺去了朝霞的体面和尊严,朝霞从呜呜咽咽的压抑变成了驴打滚式的嚎哭。
老玉看着心疼,咬牙给朝霞买了止痛针,那药实在太贵了,不到一个月,家里的钱花得底朝天。
眼看着钱成了问题,朝霞疼得死去活来,程莹干脆住在店里,为了给朝霞买药,她有时候跑几十里路揽活,别家不愿意做的针头线脑她都一股脑儿揽回来,没日没夜地赶工,她希望能多挣一份钱,让朝霞少受点罪。
半个月后,程莹因疲劳过度晕倒在店里,朝霞说,你看你何苦呢?为了一个将死的人。
程莹说我愿意。
老玉抽了半夜烟卷,她看着疼得满床打滚儿的朝霞刚刚睡着,厢房里程莹已经累得爬不起来,他狠下心,骑着二八破自行车走进了茫茫黑夜。
几个晚上下来,钱到手了,朝霞的日子总算是好过点了。
程莹换着花样给朝霞做好吃的,可朝霞吃什么吐什么,人瘦得一把干柴一样,眼瞅着没几日了。
老玉到底是被抓了现行,偷窃钢材是犯罪,好在老玉是初犯,偷的又不多,情节不算严重,关半个月就可放出来。
单位念在老玉勤勤恳恳十几年,考虑到家里的境况,只是做了处分,破例没有开除老玉。
朝霞撑着病恹恹的身子,程莹蹬着脚踏三轮车,两个人去看老玉。
见了老玉,朝霞笑呵呵说:“老玉,你能耐啊!都能蹲号子了。”说完扯着老玉一顿捶,她已经没了气力,拳头落在老玉身上,像弹棉花一样,轻飘飘没了落地的声。
老玉抓着朝霞的手,十个手指头铁钩子一样干,身体瘦得脱了人形,脸色蜡黄干枯。老玉到底是没忍住,哭得稀里哗啦,朝霞也哭,外面的程莹也跟着哭。
哭够了,朝霞说:“等着你。”
朝霞走的那一夜,老玉还被关着,她捧着腹痛,拼命煎熬着,可到底是没等到老玉。
老玉是第二天回来的,昏黄的月色里,人已经入了殓。
朝霞走的时候,身边只有程莹和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她眼巴巴地熬着,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活气,枯瘦的手扯着程莹,止痛针接不上了,她说她实在疼得等不到老玉了,她太痛苦了,早死早解脱。
程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姐,大哥明儿个就回来了,你再坚持坚持,会好起来的。”
朝霞嘴角一扯,努力一笑,她说:“阎王是判官,他叫人三更死,不敢留到五更天,命不由人啊。程莹,你不要哭,哭没有用,要笑,日子已经够苦了,再哭哭啼啼,就更苦了。往后,这个家,这群孩子,还有老玉都得靠你帮衬着呢,你不能倒下。”
程莹哭得更厉害了,她想着,那一年的黑夜,朝霞提着菜刀救了她的命,可眼下,她除了哭,却什么也做不了,连一支让她减轻疼痛的针都接济不上。
她呜呜咽咽地抽泣,朝霞攥着她的手,指甲抠进她的肉里,她知道朝霞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但程莹感觉不到疼,她也死死攥着朝霞的手,想通过那薄薄的指甲来缓解她的痛苦,可朝霞突然松了手,程莹的心一紧,听见朝霞气息陡地一转,中气十足,她说:“程莹,姐突然不疼了,这一刻,真舒心。”
程莹心下明白,这是回光返照,朝霞真的要走了。
接着朝霞说:“姐得托付你件事,你得答应姐。”
“姐,你说吧,啥事俺都答应。”
“程莹,那六个孩子,除了大俊和二海大点,都是孩子,尤其小萧,刚会说话。”
没等朝霞说完,程莹就抢着说:“姐,孩子们你放心吧,有我一口吃的就不能饿着他们。”
“不是,还有老玉,你也得管,我走了,你就跟他过吧,不要嫌弃他们,是姐拖累了你。孩子们和老玉托付给谁姐都不放心,只有你,姐最放心。”
程莹惊得半天反应不过来,朝霞突地变了脸色,腹痛像浪潮一样涌来,她的气力越来越弱,她说:“程莹,你就答应吧。”
程莹心里想,她何德何能敢答应,她有什么资格嫁给老玉那样的男人,她使劲摇头说:“姐,这种伤天理的事俺不做,俺不能做。”
“这不是伤天理,你不做别人来做了,孩子们会遭罪,俺得感谢你。”朝霞说着眼珠子就瞪圆了,程莹哭喊着,她说,姐,俺答应你,俺答应你,你不要走。
可朝霞的手彻底松开了,再也没了声息,逼仄的小院里哭嚎声此起彼伏,程莹拖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匍匐在朝霞瘦的干枯的身体上哭得死去活来。
哭够了,程莹打起精神张罗一切,好在邻居们都过来了,朝霞平素里没少接济过人,巷子口挤得转不开身。
棺材抬进来,净身、刮面、穿寿衣,大家七手八脚帮着入了殓,一切算是安顿停当了。
朝霞的寿衣是程莹亲手做的,一针一线没日没夜地缝制,老早就做好了。
岁头纸飘在巷口,哗啦啦作响,老玉还没踏进门,便一头栽倒,他知道他还是晚了一步。
朝霞一走,院子里空荡荡,程莹移了一颗杏树苗,她想着,朝霞那么爱笑,杏树一开花,院子里就有了生机。
朝霞说得对,活着已经够苦了,不能再哭哭啼啼了,后来的程莹,很少再流过眼泪,她像是被朝霞附了体一样,干劲十足。
她帮扶着老玉照顾六个孩子,日子长了,孤男寡女,两个人少不得神色接触,起先,程莹极力避让着,她生怕老玉多心。
可老玉却不回避,下雨天去店里接她,夜里她回来得晚了,他就干脆等着,遇上个雪天,老玉怕她摔了,干脆扶着她,程莹心跳得厉害,脸烫得像熨斗。
有一次,程莹发高烧,老玉在她身边守了一夜,握着她的手紧紧不放,程莹不敢动,她怕惊了老玉,又害怕失去那种感觉。
日子长了,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传进耳朵里,说什么的都有,孩子们的嫌隙大概就是那时候种下的。
有一次,她居然听见有人说,朝霞就不该留她,你看看,命多硬,自己的孩子没了,硬生生把朝霞克死,眼下,和老玉眉来眼去黏黏糊糊也不嫌寒碜。
程莹尽量避着,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小萧在巷口被推倒,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嚷嚷:“没娘的孩子,没娘的孩子。”程莹气不过,她得护着小萧,拿着扫把满巷子追着教训那群熊孩子。
张家长舌的婆子站在巷子口,嘴里的瓜子皮还没吐利索:“哎呦,这当后娘的心真切,咋地,老玉上了你的炕了?”说完一群街坊跟着笑得四仰八叉。
程莹抱起小萧,小萧从程莹的怀里挣脱,气鼓鼓地说:“不要你管,就是你,克死了我妈。”
老玉下了大夜班,自行车叉在程莹面前,说了句:“上来。”程莹愣在原地,老玉说:“上车呀,我驮着你。”
路过街坊面前,他停下来,冷哼一声说:“各位街坊,都一个区住着,知道你们对朝霞那份心思,可以后不兴你们再那么说程莹了,不是我不答应,是朝霞,她不答应。”
说完,他一手抱起倔强的小萧,车后驮着程莹,不过几步路,程莹觉得,那一天老玉却骑出千山万里路的情义。
自那之后,街坊嘴上不说,可看程莹的眼神依然是鄙视的,他们恨不得用眼神杀死程莹。
自那天后,老玉越发不避讳了,吃饭的时候会给程莹夹菜,当着孩子们的面叫程莹给他弹扫衣服上的灰。
几个孩子年幼,除了大俊懂事外,巷子里的流言灌进耳朵里,都扎进了心田。
不管日后的岁月她如何温柔地待他们、养他们、护他们,他们都跟她别着劲。
朝霞走后的第三年,老玉决定娶程莹,也没张罗着大办,街坊邻居加上钢厂里要好的几个同事七七八八请了三桌酒,就算结婚了。
新婚的那天夜里,老玉说:“程莹,你还记得那年朝霞坐着脚踏三轮车去牢里看我吗?”
程莹说:“咋不记得,她都疼得直不起腰了,还撑着骨头去看你。”
老玉叹了口气:“她那是怕自己撑不到我回家,提前去安顿后事了,那天,她跟我说,她走了,叫我风风光光把你娶回家,好好照顾你,她说你苦了半辈子,还没尝过男人知冷知热的疼惜,她是真把你当成她那死去的亲妹子了。”
程莹听老玉说完,一嗓子哭得接不上气,她想起朝霞走的那天,拉着她的手说的话,她说叫她帮衬着老玉,原来,她早就给她铺好了后路,她欠下的不止是一条人命,还有几世的恩情。
朝霞心里活的明镜似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福薄命浅。
那一夜,新婚长夜,老玉和程莹坐了一夜,唠到天明,都是朝霞。
霞莹棉布坊照例还开在老地方,尘土飞扬的农贸市场越来越繁华,外地人涌着赶进来。
老玉说,不行就换个地方,这一天天尘土飞扬的,没个好景象。
程莹不同意,她说,只有在这里,她才能感受到朝霞还在。
棉布坊的生意越来越好,程莹雇了一个机工,自己一边做裁剪一边跑出去揽活,从起初的棉被床单做到校服和单位的棉服,店面也扩张了一间。
钱挣得多,可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大俊争气,学习年年第一,研究生毕业想要去国外留学,十几万的学费,大俊不愿说,可程莹心里头知道,她不能委屈了孩子。
朝霞姐当年死活不肯住院化疗,就是想让几个孩子走出棚户区,她得替她完成心愿。
老玉不同意,他说普通的工人家庭后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决不能可着大俊一个人花钱,可程莹说,每个孩子都不会落下,大俊出国的事,她和老玉天翻地覆吵了半个月,最后,老玉妥协了。
程莹万万没想到,就是她那句每个孩子都不会落下,惹出了事端。
大俊出国后,几乎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下了好些外债,紧接着,便是二海,二海学习差,天天不是打架就是逃学,高中没毕业就跑出去闯社会,混了几年,回来了,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不成器。
眼瞅着到了结婚的年龄,程莹急得团团转,她和老玉商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给二海谋了个正经营生。
二海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追女孩是厉害的,媳妇领回来了,程莹高兴得合不拢嘴,好酒好菜地张罗,姑娘虽说打扮得花里花哨,可愿意跟着二海,程莹就开心,倒是老玉,一天到晚,哼哼唧唧骂骂咧咧看不惯。
临着年关,家家户户张罗过年,程莹算了算,想给大俊寄点钱,她心想,好出门不如歹在家,几个孩子都守在身边,就大俊远隔重洋,心疼得多了点。
二海不愿意了。
“程姨,到底是不一样啊!这我妈当年把大俊给了你,你还真拿他当亲儿子养了,这我妈要是活着,我这婚事能不上心?”
“你想咋滴?”老玉吼。
“要钱啊,娶媳妇彩礼钱买房子的钱,你们给了吗?可着家里的钱都让老大独吞了?”二海一甩分头,趾高气昂地冲着程莹喊。
老玉是急脾气,他退休了,满世界捡破烂,刚捡回一三轮车破铜烂铁废纸篓,说话间操起一块废钢就朝着二海砸去:“你个不成器的玩意儿,怎么说话呢?”
废钢落在二海的脑门上,血溅得到处都是,二海手捂着脑门连嚎带叫,老玉心底有些害怕,但嘴上还不减气势,仍然大骂:“老子打不死你。”
程莹忙跌跌呼唤:“老三,老四,快些带你二哥上医院,打破伤风。”接着回头呵斥老玉:“你是老糊涂了,怎么啥都往脑门上甩?”
老玉泄了气。
好在二海伤得不严重,打了破伤风回来了,鸡飞狗跳的小年算是过了。
那一夜,程莹答应了二海的彩礼和房子的首付,那年头,虽说彩礼不多,房子不贵,可架不住孩子多,二海的婚事还没落停,紧跟着老三老四又考上了大学。
程莹和老玉像两头低头拉犁的老黄牛,没一刻有歇下来喘气的功夫。
老三老四一毕业,工作了,以为能松口气,老五和老六跟着长大了,年年花钱的地方像开了闸的洪水,涌着浪,一浪接一浪。
老三是女儿,房子和彩礼不用,可结婚的陪嫁不能寒碜,街坊邻居没事总笑话程莹:“一天天能耐的,开个破店,掂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棚户区的穷孩子,可着就她家的金贵,你见过女儿出嫁嫁妆那么多?”
众人摇头,嗤之一笑,不屑里塞满了妒忌。
程莹不管,她累死累活,也得叫孩子们离开棚户区活出个人样,朝霞拿命换来的恩情,她做这点不过九牛一毛。
几个孩子拉扯大了,她也一天天老了。
缝纫机蹬不动了,她舍不得卖,院子里当年的杏树长粗实了,花一开,风来,摇落满地,程莹恍惚,五十年忙忙碌碌一眨眼过去了。
她叫老玉围了板子,小小的杂物间,陈旧的缝纫机、案板、锁边机都是当年朝霞置办下的,后来出了新式的,程莹都没再置办,老设备像旧人的影子,一朝一夕都是气息,她害怕岁月磨损,让她忘记了朝霞,逢年过节她进去擦拭一番,机油一打,踩几下呼噜噜转。
朝霞的笑声还在:“哎呦,这手艺,是要饿死师父呀!”
棚户区改造的文件下来,程莹哭了几个晚上,她不愿意搬,老院子有朝霞的影子和当年的回忆,可又盼着,朝霞苦了半辈子,老玉和她也苦了半辈子,搬新家不是好事吗?
程莹想通了,带着朝霞一起走,三轮车上,她抱着霞莹棉布坊的老伙计住进了新房子。
“夜里凉,您也不盖着点。”
程莹歪在躺椅上迷迷糊糊听见一个声音,猛地睁开眼,吓了一跳,眼前的人微微发福,一副中年人模样。
“大俊?!”她失声喊。
“妈。”
一声“妈”,程莹咬着唇,她不敢哭,这辈子,她风里来雨里去,没明没夜地蹬脚踏板的缝纫机,六个孩子养大了,五十年了,没人叫过她一声妈,大俊突地站在眼前,这一声妈,叫得程莹万箭穿心七上八下,她觉得这是梦。
她不敢哭出声,她害怕醒来,醒来多可怕,有家回不去,男人躺在ICU,生死不明,就这样,不说话,匍匐着歪在走廊冰凉的躺椅上,感受一点温情,有儿女的温情。
“妈,您怎么了?”大俊俯下身关切地询问。
“大俊,这是不是梦?”程莹抬起头问。
“妈,是真的。”大俊用大衣裹紧程莹,程莹抓着大俊的手呜呜咽咽抽泣,哭着哭着她说:“大俊,你咋回来了?那么远?”说完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老糊涂了,老玉都病成那样了,大俊能不回来吗?
程莹没敢和大俊说家里换了锁,她怕大俊难受,这些年,大俊不说,她也知道,他在国外过得也艰难。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
几个兄弟姐妹把大哥从国外叫回来,并不是商量着怎么给父亲看病,而是征询老大的意见,放弃治疗,后续的费用实在太高,八十多岁的人了,就算是醒过来也活不了多少时日,家里的房子还有存款,几个商量着分了,至于程莹,他们只字未提。
大俊听完弟妹们七嘴八舌的意见,良久,他才说:“你们知道爸和妈的存款有多少?”
“妈?大哥,你自己没妈吗?叫得这样亲切,她可是抢了爸的人。”小萧气恼地质问大哥。
接着二海附和道:“大哥,你这留几年洋,就是不一样啊,咱是商量爸的后事,你管她干嘛?”
“爸的后事?爸还没死呢?”大俊突然提高了嗓门,接着他一把扯过小萧说:“小萧,这里边你最没资格说话了,妈走的那年,你才不到三岁,是谁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你不知道吗?”
“你们一直觉得是程姨克死了妈,抢走了爸,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咱们棚户区那个烂光景,除了程姨谁愿意接手?妈的病是绝症,你们好歹也算是念了书的人,怎么分不清楚个是非黑白?”
“算算吧,这些年,咱们几个,出国、读书、结婚、买房子,哪样不是程姨一路和爸用命拼着又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你们回头看看,棚户区有多少孩子像咱们一样,你们的良心呢?他们在那憋屈的地方窝窝囊囊住了一辈子,临了分了套房子,我们几个再给分了,妈在地下能答应吗?”
大俊激动地说着,嗓音哽咽,他想起那一年,他妈病的那个雪夜,程姨背着他妈,三步一摔五步一跤,他借的三轮车被雪卡着走不动,是程姨使尽力气抬着和他去的医院。
后来,程姨为了给她妈多挣点买止痛针的钱,几十里跑去农村揽活,大冷的天双手都是冻疮,在店里蹬缝纫机,半个月累到吐血。
大俊的话还没说完,二海就扬长而去,小萧不敢再吱声了,其他几个没了气焰,大俊说:“爸的病还得治,程姨将来我养着,她就是我妈。”
大家不吱声了,原来老玉的存折和身份证都在老三手里,她交给大俊的时候,脸色铁青。
程莹没想到,原来这几个孩子早就打算好了,她还蒙在鼓里,要不是大俊,她可真的就差饿死街头了。
老玉在ICU住了七天,总算醒了。
他看见大俊隔着万里重洋回来看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老玉一天天好起来,捡破烂的营生程莹再不叫他干了。
有一天夜里,老玉突然心血来潮,拉着程莹的手说:“让你看个东西。”
神神秘秘的,原来是房产证。
程莹说:“你弄这个干嘛?”
老玉说:“你知道吗?我住院的那些天,清醒的时候,给大俊打了电话,叫他回来把房子过户到了你的名下,还有那些存款,你总说自己不认识几个字,都存在我的名下,我也都让大俊转存在你名下了。”
“若我活着,你有我就有,若我死了,你自己有才能有保障。”
“你跟了我半辈子,苦苦寒寒,帮我拉扯大一群孩子,我不能叫你老了老了还无所依靠吧。”
程莹听着老玉的话,眼眶湿润,她心底里想,原来她也是个有福气的女人。
主播:如初/大威
编辑:阿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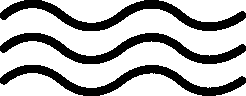
“她不爱我,却想和我结婚”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每天读点故事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