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的母亲抛下我,跟别人私奔了
冯自珍想不通,母亲为了一个老头儿,竟然那样亏待自己。
如果三十岁的她都能看透爱情的虚幻,母亲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想要折腾什么呢。
下了出租,拖着箱子穿过石板铺就的小巷,冯自珍终于找到了家。
花田坊189号,刚才差点儿连地址都想不起来。
熟悉的黑色的木门、青砖院墙和半截可见的转角楼梯,可让她意外的是,门上却多了一盏筒灯,上面黑色的幼圆字体印着“珍珍民宿”。
冯自珍想起,母亲在电话里提过想开民宿,可是她没同意。
一来母亲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她不认为她应付得了。
二来民宿挣这点儿钱有什么意义呢?江城这种小地方,她每个月给她五千块钱还不够花吗?
其实说到底,冯自珍还是讨厌那个姓蒋的老头儿。
自打母亲跟他在一起后,就总能冒出各种“点子”来,说要借钱给他儿子看病,帮他买出租车、买房,甚至还提过一次要和他结婚。
好在不管怎么说,在所有“大事”面前,母亲还是很听冯自珍的话,只要她不同意,她总能打消念头。
母亲从来都是心思单纯且有些愚笨的人,从外公到冯自珍的父亲,都将她的单纯保护得很好。
冯自珍高二那年,父亲见义勇为牺牲了,母亲受了很大的刺激,一夜之间性情大变,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人也变得迟钝。
冯自珍只能站出来,处理父亲的后事,还有大大小小的琐事,把伤心的母亲护在自己身后。
一直以来,母女关系似乎是倒过来的,冯自珍是强大的那一方,而母亲更像个小姑娘。
父亲牺牲后,算上他的抚恤金和各类奖金补贴,再加上母亲“交”上来家里的存款,这个家共有二十一万。
钱是打在母亲银行卡里,可是卡一直在冯自珍手上。
一如父亲从前那样,她每个月给母亲三千块钱家用,剩下的就由她来保管。
上补习班、上大学、买书和电脑,该花的她一分不少,不该花的她也绝不浪费。
她会细细地记账,有大的支出也会跟母亲商量,虽然母亲从来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父亲在世时总是用“军事化”手段来教育冯自珍,那时候她叫苦连天,可是现在看来,命运似乎有它的深意。
冯自珍推门进去,原来破旧昏暗的客厅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靠墙壁电视柜的地方如今是前台,鞋柜变成了一只软沙发,顶上的灯是换过了,三个圆框叠在一起,被银色丝线环绕着,透亮而温暖,壁纸也是棕白条纹渐变,显得很有情调。
“珍珍民宿欢迎您!”一个年轻女人迎了过来。
小鼻子小眼,笑容比她脑袋上的灯还要灿烂。
“有预定吗?”她问。
“没有。”冯自珍道 。
她想给母亲一个惊喜,可是明显不合时宜。
“不过还有两间空房。”女人道,“都在楼上,而且是江景房,很多客人都喜欢。要不要看看?”
冯自珍点点头,将手机先揣进了兜里。
现如今,二楼和三楼的房子都被收拾成了客房的模样,新的家具和灯具,各个房间风格不一样,但也很是温馨漂亮,而且原来楼梯拐角的地方还加上了电梯,可以直达四楼天台。
“怎么称呼您?”冯自珍问。
“我叫何美姿,你叫我小何就可以。”
“你是民宿的老板?”
“不是老板,算管理者吧!我们还有打扫的大姐和一个厨师。”
“这幢楼是你们租来的?”
“对,老板本来想买的,但是房东不卖。”
“都是老居民,没人会卖吧?”
“有呢!我们老板这两年买了四五幢了,都在附近。虽说这两年花田坊在开发了,但前景不好说。这些都是老房子,附近教育和医疗资源又不好,加上现在房地产市场也没前两年火爆,还是有人肯出手的。”
“像这样的能卖多少钱?”
“三四百万吧!毕竟是五线城市,又处在郊区,也就眼下旅游还可以,以后谁知道呢!”
“租呢?”
“具体价格就不方便透露了。”
“一年十万总有的吧?”
小何微笑着犹豫,终于点了头,“差不多吧。”
跟小何聊得久了一点儿,冯自珍突然很想住在这里。虽然母亲不在这儿,但这还是自己的家啊。
“行,我要二楼那间吧,加上早餐。”
“好的,住多久?”
“先开一晚上吧,有需要我再续。”
坐在熟悉却陌生的房间——奶奶以前的那间房里,冯自珍竟觉得平静。
她终于拔打了母亲的电话,对方却关机。
母亲从用手机起就会在睡前关机,说是怕有辐射。
冯自珍给她说过不会有问题,可她总是不信。
微信自然也是联系不上的,她后悔没有在回来时提前给她打个招呼。
她住到哪儿去了呢?冯自珍不禁胡思乱想起来。
以她对母亲的了解,她不认为她有和别人谈判,并把整幢楼租出去的能力。
她大概也不会再买套房,或者自己租套房,以前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又去了哪里?
虽说也没什么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总有些是要留下来的吧,比如父亲的几样古玩儿,或是冯自珍从前弹过的古筝。
冯自珍与母亲的关系多少有些微妙,好像很难亲呢起来。
冯自珍觉得母亲有些愚钝,很多事情不是很好沟通,她也就懒得沟通。
她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结婚、买房、离婚,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她的意见,母亲甚至连孙承达的面儿都没见过。
好像没有那个必要,她早就习惯了冷漠的母女关系。
冯自珍想起那个姓蒋的老头儿,不由得生起恨意来。
一准儿是他给母亲出的主意,房租一年收十来万,再加上冯自珍给母亲的钱,母亲一年能落近十万。
她以前只想母亲自己手上宽裕一些她就能轻松自在一些,若是全被那姓蒋的老头儿卷了去,只能怪自己疏忽大意了。
冯自珍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在一家银行工作,随着职位的升迁工资也在增长,几年下来,怎么说都算小白领了。
工作近十年,她攒出了一套小居室的首付,只可惜那时候她和孙承达已经领了证,结果离婚后卖了房子也不得不分他几十万,简直亏死。
休假回去又得重新租房子,单是想想就觉得头大。
孙承达比冯自珍小了四岁,是个所谓网络策划,其实就是个不红的网红,因为长相优越,又能说会道,所以平时拍拍视频,赶一些乱七八糟的活动。
冯自珍结婚确实是草率了一些,三十好几,被工作折腾得苦不堪言,遇上孙承达,仿佛被人从水里捞了出来一般,被他逗笑,被他的乐观所感染。
她也从他身上知道,原来生活的轻松跟金钱的关系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大。
从恋爱到结婚,三个月全部搞定。
买房、装修、家具电器,也全是孙承达在跑。
在听话这个方面,孙承达简直跟冯自珍的妈妈有得一拼。
冯自珍要说壁纸要米黄色,孙承达立刻就说他选的蓝色太闷。
冯自珍说整体厨房不划算,还是自己设计再单独购买性价比高,孙承达立刻想办法去退整体厨房的定金。
和周围龟毛挑剔的金融男比起来,孙承达像天使一样可爱。
可是婚后生活在一起,冯自珍慢慢觉出不对劲。
起先是他突然多了很多出差的机会,也更爱跟朋友出去玩儿。
冯自珍工作忙,对家庭生活也不太操心,直到一年后,一个男人找上门来,说他是孙承达的男朋友。
离婚也撕扯了好一阵子,因为孙承达出过一些装修和家具电器的钱,两人掰扯不清,差点儿闹到要打官司。
冯自珍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个闲功夫,最后咬碎了牙和着血咽下去,卖了房子分了钱,两人也算一拍两散了。
只是可惜了那只叫繁花的猫。猫留给孙承达了,而且听说它怀孕了。
孙承达的微信是删了的,繁花大概连照片也看不到了,希望它和肚子里的小猫都好,冯自珍真诚地许愿。
虽然掏着一晚上三百六的房费,可到底是自己家,冯自珍这一晚睡得很好。
她起来第一件事是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手机开机了,却无人接听。
她简单地洗漱,去一楼吃早饭。
可是她怎么都没想到,一楼卫生间里走出来系着围裙的妇人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母女二人面对面怔在那儿,冯自珍叫出一声“妈——”
母亲这才小声问道:“珍珍,你怎么回来了?”
“我昨晚回来打你电话你关机了。”冯自珍扔下牛奶杯,“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闲着没事儿,干点儿活。”
“你干什么活儿,我给你的钱还不够你花吗?”冯自珍一股怒气冲上心头,上去就摘母亲的围裙。
母亲尴尬地站着,任由冯自珍忙活着。
吃饭的客人都在回头,小何被引了出来,忙问怎么回事。
“你们到底给多少钱还带让房东在这儿干活儿的?”冯自珍问。
“什么房东?”
“你别跟我装傻!我告诉你,这是我家的房子,这是我妈。你把租房合同拿来我看看!”
小何的脸变了颜色,“她不是房东啊!冯东是个大爷。”
“你最好现在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如果是别人冒着我们的名儿签合同,这后果你知道的吧?”
小何慌里慌张地去打电话,冯自珍瞪着母亲,低声问她,“怎么回事儿?”
“我就是整天坐着腰疼,就想找点儿事儿也活动活动。这儿活轻,又不累——”
“楼上楼下三层,你一个人打扫,这叫不累?”
“我一早上就弄完了。”
“你住哪儿?”
“我住的离这儿也不远,走半个小时就到了。”
“你租的房子?”
“蒋,你蒋叔叔的房子。”
冯自珍气不打一处来,果然是被姓蒋的坑了。
小何跑了过来,给冯自珍看手机上拍的租房合同。
冯自珍哗哗翻到最后,的确是母亲的签名“赵唯华”,而且也是她的字迹。
“合同是公司签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您能拿出房产证,如果证上的人跟我们的合同不符,公司说他们会派人过来处理。”
“你签的?”
母亲怯怯地点了头。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边联系过的房东是个叔叔,而且阿姨也是那位叔叔推荐过来的,哦,对了,我们民宿的名字也是那位叔叔要求的。”
冯自珍气得冒火,立刻就拽着妈妈,道:“走,你现在带我去见那个姓蒋的老东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把你玩儿得团团转!”
“你们结婚了吗?”在出租车上冯自珍问道。
“没有,当然没有。”
“那算同居?”
母亲不说话。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她们母女一眼,眼神多少有些看热闹的热情。冯自珍也便不再问了。
一处老旧的工厂家属院门外,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铁栅栏门旁左顾右盼、神色慌张。
出租车还未停稳,母亲说,“他就是蒋山川。”
冯自珍看到了他的脸,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母亲先下车,蒋山川立刻就满面笑容迎了上来。
冯自珍跟下去,满肚子的气在他的笑容前也都不得不先收起来。
“珍珍刚回来,我带她来看看你。” 母亲表情有些尴尬。
“哦,走,回家里去。”
冯自珍黑着脸一言不发,跟在他们身后走进铁栅栏门。
蒋山川走路的时候有些颠,像是腰和腿都不太好。
院子里的家属楼相当老旧,墙上也随处可见各种告示和小广告,角落的砖有脱落的痕迹,细窄的小花园似乎也无人打理,总之,一切都是破败之相。
“上次见珍珍还是她上大学的时候。”蒋山川说。
他的寒暄相当自然,可是冯自珍怎么也想不起来见他的场景。
“是吗?在哪儿见的?”冯自珍毫不客气地问道。
“远远地看,就看看你。”蒋山川神色慌张,“不过小时候也见过你,你肯定不记得了。”
一时间,冯自珍着急了。
那时候爸爸还在,难道他们那时候就在一起了?
可是再看看走在前面的母亲,她那样老实胆小又木讷的人,怎么可能干得出对不起爸爸的事情。
在楼洞口,冯自珍停下脚步,质问道:“你到底是谁?”
蒋山川看向母亲,满眼疑惑,“珍珍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我都没给她说过。”母亲怯怯道。
“跟我说什么?”
“珍珍。”蒋山川向前一步,“我跟你爸爸是同学,多年前就认识。你爸爸当兵去了,我进了工厂。”
他回头看了眼黑漆漆的楼道,“说起来话就长了,咱回家说吧?”
冯自珍点了点头。
防盗门打开,蒋山川朝里面喊了一句“小刚——”
冯自珍瞥一眼母亲,母亲便解释道,“小刚是蒋叔叔的儿子。不过,他身体不大好。”
昏暗的客厅里,酸腐的气味中,一个巨大的身影慢吞吞摇了过来,无声无息,像夜晚的海浪,带着些骇人的气息。
冯自珍在母亲身旁站着,看着这个浑然大物,像一只警惕的小鹿。
蒋小刚在冯自珍眼前站定,低头看着她,眉压着眼睛,显出一些凶相。
冯自珍听见他喉咙里“呼呼”的声响,迎上了他的目光,她也终于意识到,他的目光里有种混沌的东西,与常人大不相同。
“我带小刚进去,你带珍珍先坐。”
蒋山川拉他,蒋小刚却岿然不动。
蒋山川拍了他的背,又上前拉扯劝慰,他发出几些奇怪的声音,终于跟着父亲进去了。
母亲陪冯自珍在沙发上坐下,道,“小刚从小有自闭症,跟别人不一样。”
原来如此。
“今年开春时他把蒋叔叔一把推下了楼梯,胳膊腿都骨折了,住了一个多月医院。”
看他们父子的体型,冯自珍也猜得出伤得不轻。
她被蒋小刚惊讶到了,可她还是努力镇静下来,冷冷问道,“你来说还是等他出来说?”
“说,说什么?”
“他跟我爸是同学,然后呢?”
母亲低下头,竟有些害羞。
“让我猜猜,他俩都喜欢你?你选了我爸?”
母亲躲着冯自珍的目光,竟意外地点了头,“那时候能嫁给解放军,是很光荣的事情。”
“可是你喜欢蒋山川?”
“也不是。那时候才还不满二十岁,我也不知道喜欢谁。你爸去部队前让我嫁给他,我就同意了。蒋山川的心意我看出来了,可是他没说过那个话,后来就算了。唉,那个年代,跟你们现在的人不一样。”
“嫁给我爸你后悔了吗?”
“没有,没有。”母亲连连摆手,“你爸对我很好,对你也好。”
打从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部队,只有放假才会短暂地回来住几天,可是对她依然严厉。
冯自珍上初中时父亲才转业回来,三四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父女关系变得亲近,父亲就牺牲了。
可他依然是父亲,冯自珍依然对他抱有特殊的情感。
“那你们以前有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爸的事儿?”冯自珍冷眼问道。
“没有。”从黑黢黢的过道里传来一个声音。
蒋山川走了过来,道,“从来没有。”
蒋山川依然记得他再见赵唯华时的场景,她扎着羊角辫,穿一件红格子衣服,还戴着白色的袖套。
她在供销社给人帮忙,对每个人都笑意盈盈。
他们住得并不远,小时候也都见过,还一起玩儿过。
可是未曾留意,她一夜间长大,突然就出落得这般标志。
蒋山川去买一包盐或是一根笔,就是想跟她多说两句话。
笔买回去不敢用,第二天又去换,见她一面总是高兴的,却怕她把自己当成斤斤计较的人。
蒋山川与冯桐光整日形影不离,他们每天上下学从供销社门口过,他的心思必然被冯桐光看出来了。
可他从来不问,在赵唯华面前也不动声色。
倒是蒋山川自己有意无意提起,不吝惜与冯桐光分享心事。
两人一起报考军校,只有冯桐光入选,蒋山川因为个子矮了一点儿落选了。
当时工厂扩招,而且效益不错,蒋山川便进了工厂。
冯桐光入伍那天,蒋山川一直送他到火车站。
他不断地替他整理胸前的红花,心里万般不舍却说不出口。
而冯桐光看起来也很沉闷,好多次想要说些什么的样子,却始终没有开口。
蒋山川进了工厂的第三个月,他拿到了一笔季度奖。
他买了烟酒和几样糕点,终于鼓起勇气敲了赵唯华家的大门。
赵父是个和蔼的老教师,听说对这个小女儿相当疼爱。
当蒋山川讲明心迹时,却怎么也没想到,赵唯华已经和别人订亲了。
“也是不巧,就前几个月的事儿。因为女婿急着入伍,订婚宴也很匆忙,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唉,他们自己愿意,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拦着。”
蒋山川的脑袋嗡嗡作响,像被人塞进笼子里沉到了江里。
“谁,谁啊?”蒋山川哆嗦问道。
“桐光,冯桐光。”
蒋山川记不起来自己是如何踉跄着爬出赵家,又是如何压着恨不得立刻将冯桐光撕成两半的火气。
怪不得他不动声色,怪不得离开那天欲言又止,原来他心里揣着那么个惊天的阴谋。
冯桐光新兵训练时给他写过一封短信,不过关于部队生活尔尔,可是训练结束,他又去了新的地方,还未联系上。
蒋山川的怒火无处爆发,他去找赵唯华,抓着她的袖套将她从供销社拉出来。
“你订婚了?”他瞪着她。
她像被吓坏的小动物,除了点头,什么也不会说。
“你想跟他过吗?”
这句话,几乎是蒋山川最后的希望,可是赵唯华还是点了头。
当他看着因为惊吓而满脸通红的可怜姑娘,他觉得自己像个混球儿。
他本来想要表明心迹并将她抢过来的,可是面对她时,他知道一切不可能了。
在民风淳朴且有些传统的江城,婚姻大事,哪能这样出尔反尔的?
而且如果能嫁给军官,她又怎么愿意重新去选择一个工人?
蒋山川什么话也没说,转身离开了。
无论痛苦还是怒气,他都只能憋在心里,这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已经没有关系。
后来,他又收到冯桐光的信,他知道他去过赵唯华的家里,也知道了他们的事。
他写了满满六页的信,说他的情难自抑,说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字里行间也全是歉意。
蒋山川将信撕得粉碎,揉成一团投进江水里。
他看着那团白纸被江水冲开,像花瓣一样慢慢散去。
从此,他再也没有理会过冯桐光,也没有理会过赵唯华。
很快,蒋山川也结婚了,新娘是郊县一户农家的女儿,干干净净,也很精明。
即使没有当年对赵唯华的心动,他对新娘也很有好感。
日子慢慢朝前推,他们有了儿子小刚,蒋山川也有了分房的资格,工厂效益不错,妻子也在子校的后勤找了份临时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也平静且温馨。
还是幼儿园的老师先发现的,小刚似乎跟别的孩子很不一样,他迟迟说不了话,行为模式也很怪异。
蒋山川带小刚去过好多家医院,他第一次知道“自闭症”,小刚也被确诊了自闭症。
正常学校不肯收小刚,妻子只能辞职在家照顾他。
可是日复一日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小刚的语言和行为能力没有一点儿进步,反而常常出现暴力倾向。
小家庭的氛围急转直下,他们开始争吵,抱怨,互相咒骂。
终于,在小刚六岁时,妻子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带着家里所有的钱离开了。
在最黑暗的时刻,冯桐光在别处听说了故友的故事,带着大包小包和五百块钱出现了。
他们喝了一夜的酒,现实的困境解开了过去的矛盾,痛苦溶解在了酒里,往事也随着酒精挥发。
他们重修旧好。
“过去的很多年,你爸一直在帮我,一放假就来找我,部队发了东西他都直接寄给我,还给我寄钱。他转业回来后帮的就更多了,时间长了,我们的关系也缓和了。”蒋山川道。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冯自珍看向母亲。
“你也只是个孩子,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大了你也没告诉我。”
“没办法告诉你。”蒋山川道,“当年你爸爸牺牲,我本来想去看看你,可是你妈不让。因为你爸爸舍命救下来的人,就是我和小刚。”
冯自珍脑袋“嗡”一声响,心里一沉,浑身都颤抖起来。
蒋山川永远记得他带小刚去跳江的那一天。
小刚被查出了心脏病,医生说做动手术要花十几万。
那阵子厂子效益不行,很多工人都下岗。领导照顾他,给他留了个饭碗,可是工资却少得可怜。
满足日常的温饱已不容易,哪还有什么积蓄。
整个夏天,蒋山川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四处奔波筹钱。
平日里还客客气气的亲戚朋友,一听到要借钱都变了脸色。
除了冯桐光一口答应下来能拿五万外,跑了快一个月,也就凑出了万把块钱。
而且他知道,这是冯桐光家所有的钱了,那是他给女儿攒着上大学的钱。
那个夏天的雨似乎没完没了,下得蒋山川的心都凉透了。
心灰意冷之下,他给冯桐光留了个字条,带着小刚去了江边。
小刚从小喜欢去江边玩儿,可是他太胖,又有语言障碍,蒋山川从来也没教过他游泳。
那天,他给小刚买了他爱吃的炸鸡,还给他喝了可乐,这些都是平时不让他吃的东西。
小刚开心地吃完,还想要。蒋山川告诉他,下去游一圈儿就再给他买。
蒋山川水性很好,小刚也见过他游泳,可是小刚不知道自己不会。
蒋山川先跳了下去,没一会儿,如蒋山川所料,小刚也跟着跳了下来。
小刚先是在水里扑腾着,可是除了水声,他听不见他的叫喊。
他看着小刚那颗大脑袋时不时地冒出来,看着水花也越来越小,他努力回忆着生活的苦难,强忍扑过去救他的冲动。
蒋山川就那么看着他挣扎,看着他走向解脱的彼岸。
“小刚,只要几分钟就好。几分钟后,你就感觉不到痛苦了。” 蒋山川握紧了拳头,心如死灰,“也许,顺着江漂下去,才是咱们父子最好的归宿。”
蒋山川原想等小刚不动了,他也跟着漂下去,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随着“噗通”一声响,一个身影跳了下来了,一点一点靠向小刚,将他拖上了岸。
小刚那么胖,力气又大,有好几次,那个人都要被小刚拽进水里,可他还是不放弃,挣扎着冲向岸边。
是冯桐光!
他们上高中时多少回一起在江上游泳,蒋山川只需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那时候,蒋山川已经快没有力气。
他无法从冯桐光手里把小刚夺回到江里。
残存的意志告诉他,冯桐光来救小刚,大概是老天爷的意思,那这孩子就命不该绝,将来是被送给人还是交给福利院都由他去吧!
他不想再陪着他了,他陪不动了。
可是他知道,冯桐光不会轻易放弃他,他曾是军人,他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朋友软弱求死?
为了避开冯桐光,蒋山川咬牙游到了江心深处,然后撒开了手脚,顺着江水漂流,任由自己往下沉。
他看着团团的乌云和白花花的天空,耳朵在江水里听到一片宁静,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可冯桐光还是冲上来了。
当蒋山川因为被拉扯而恢复意识时,他已经被冯桐光拦腰朝岸边拖去。
他已经力气全无,大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像块儿木头一样被水追逐,只有冯桐光像根绳子一样拉着他,与水流苦苦抗争。
一个浪打了过来,他们被推下去好远,连在一起被水流快速推动。
也不知漂了多久,蒋山川的后背被重重一击,他撞在了江中一块儿大石头上。身体一个侧翻,石头下的水草挂住了他的腿。
当他反应上来时,腰间的那根绳子却松开了。
当他趴着石头向下看去时,冯桐光化成了一个小点儿,随着江面起伏了几下,便消失不见了。
除了白花花的江面,他什么也找不到。
冯桐光不见了。
他终于听到一些声响,是岸边人群的呼喊声,是消防车的喧闹声,可是江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
冯自珍只知道当年父亲是为了救落水群众而牺牲,可是被救的人却从来没有现过身。
她甚至还在母亲那儿抱怨过,他们怎么不懂感恩,没想到竟是母亲故意隐瞒了这一切。
“那阵子你爸跟我说小刚被查出了心脏病,动手术要花十几万,他想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帮小刚。
“可是我不愿意,就跟他吵了一架。那天你爸说联系不上蒋叔叔,一时恼火喝了些酒,后跟我又吵了几句,跑出去就再没回来了。
“等我再见到他,就是那个水里泡了几天的尸首了。”
母亲痛哭起来,就像从前刚得知父亲去世时那般悲痛。
冯自珍上前握住她的手,是久违的触感和温度。
“怪我,都怪我!”蒋山川老泪纵横。
冯自珍含着满腔的悲愤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却不知道如何将气发出来。
她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生疼。
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蒋山川竟从凳子上滑起,“噗通”跪在了她面前。
“我对不起你们娘俩。我给你妈磕过头了,却从来没有面对过你。是我害死了你爸,是我害得你们阴阳两隔,该死的是我啊!”
母亲扑过去扶蒋山川,扶不起来,就与他哭作一团。
两个头发花白之人那样失声痛哭,冯自珍却坐在那里,听着他们悲凄的声音,浑身颤栗。
原谅与否,似乎不再是个问题,在他们的故事里,她是最边缘的那个。
哪怕蒋山川跪在那里,自斥因为他的缘故让她失去了父亲,可是想来,她似乎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痛苦。
哪怕曾经为之痛苦过,如今也被岁月冲刷成了苍白。
那年,蒋山川也跪在赵唯华面前久久不能抬起头来。
他不敢奢求她的原谅,因为他知道这是无法被原谅的罪孽。
他更希望赵唯华打他或者骂他,哪怕能一时缓解他的痛苦,让他怎么样都行。
可是除了哭泣,她什么也没做。
他就那样一直跪着,用头撞着地面,等待着她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应。
“好好活下去。”他听见哭声中那个细若游丝的声音。
如果冯桐光拼了命的要救他们父子,那他们就不该辜负他,就该在这个世上好好活下去。
他懂了。
蒋山川做到了,他带着自闭症的儿子,应对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他干过工地、摆过地摊、开过黑车,甚至还当过黄牛,最艰难的时候,他用尼龙绳把蒋小刚绑在家里,一天打三份儿工。
为了给蒋小刚做手术,他欠了十几万,其中还有几万是高利贷,他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像愚公移山一样一点一点地去还钱。
而蒋小刚的病也不是一次手术就能好的,后续的治疗还要不断花钱。
除了蒋小刚,赵唯华母女成了他在这世上最关心的人。
冯桐光因他而死,他似乎就该对他妻女的幸福负起一定的责任。
他不敢直接面对赵唯华,更别提什么都不知道的冯自珍了。
可是逢过年过节,他都会偷偷送些东西去,一篮子鸡蛋、一些糕点或是市场上卖得好的小吃。
他还会塞些钱或是留几句安慰的话,可她从来没给过他回应。
起初,她连他的钱和东西都不肯收,可他依然坚持。
直到有一年中秋,他送过去的月饼没有再被退回来,他激动了好多天。
冯自珍上了大学后,当蒋山川又一次送了一桶油和一袋米过去时,赵唯华正好走出来,说:“帮我搬进去吧!”
两个孤独的灵魂,在相互的同情与孤独中,慢慢产生了感情。
他们说的话越来越多,也会互相提供帮助。
蒋山川帮赵唯华换灯泡、通马桶,蒋山川忙不开的时候,赵唯华会过去帮他照顾小刚,做做饭、收拾收拾家里。
直到冯自珍研究生毕业,他们才终于有勇气牵手走在一起。
可是赵唯华却总不敢认真地在女儿面前讨论这件事。
“这么些年,我不愿意管家里的钱,一来是我不会管,二来我怕钱在我手里,我会因为不忍心把钱都给蒋叔叔,可是这样对你不公平。钱多钱少,那是你爸该给你的。”
冯自珍从母亲的泪水里读到了她的矛盾。
一个给他温暖的男人和一个远方的冷漠女儿,她用她那颗并不聪明的大脑努力平衡双方,最后却委屈了自己。
“去年小刚又要做手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把房子签了出去。房子以后是你的,我肯定知道,所以只签了最少的年限,五年。你在上海安了家,也很少回来,所以——”
母亲像个做错了事被抓包的孩子,满眼都是愧疚。
而蒋山川挨着他坐着,他们两人的手就那么自然地握在一起。
冯自珍没有接话,她突然想到一个叫相濡以沫的成语。
自她上大学离家后,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她从没想过母亲一个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寂寞,也就未想过蒋山川给她的关怀有多么珍贵。
她想起前几年在电话里也提过让母亲再找一个伴儿的话,她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也许那个时候她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只是她不敢说出来。
她为自己与母亲的疏离感到惭愧,原来她的世界发生了这么多事,她竟全然不知。
“手术钱,还够吗?”她忍不住问道。
“房租是半年一付的,所以就先借了一些钱,只能慢慢给人家还。今年蒋叔叔摔伤了,不能工作,住院还花了些钱,所以我才去民宿那儿干点儿零活儿,等手上宽裕了就不去了。”
“我每个月给你的钱呢?”
“蒋叔叔说那个钱不能动,都留着呢,在我的卡上,你一年给我六万,有快五十万了。”
“都出去借钱,为什么不动这个钱?”冯自珍有些意外。
“你在上海开销大,人生地不熟的,怕你突然有事儿要应急。”蒋山川道。
冯自珍点点头,没有再说话。
漆黑的走道里传出“咚咚”的砸门声,蒋山川突然跳起,说“我去看看小刚。”
他扶着腰跛着脚又走进那一团漆黑,砸门声也随之消失。
冯自珍看了眼母亲,看到了她眼里的关切。
她已经与他们父子连接在一起了,而那份连接里有痛苦和无奈,也有很多的温暖。
江水又涨了。
好在天气还不错,冯自珍和母亲在江滨大道并肩前行。
不远处就是花田坊,冯自珍能看到自家红色的房顶,在蓝天白去之下,有种岁月的温情。
“我不反对你再找个老伴儿,但我不想你跟着别人受苦。”冯自珍说。
“蒋叔叔不是别人,我们年轻时就认识了。”
“如果他比我爸先向你表白,你是不是就嫁给她了。”
母亲看了冯自珍一眼,点了头。
“以前的江城,那么大一点儿,人也很少。一起长大的这些人,彼此都认识。
“你爸和蒋山川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怎么选。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么有主意。
“就是有时候想,如果我跟蒋山川结婚了,他是不是就不会被小刚拖累了,可是又想,那你爸会不会生下小刚那样的孩子,唉,反正怎么想都不对。
“我们这些人啊,就像一个树杈上长出的叶子,都是连在一起的。”
冯自珍无法理解那样的感情,在上海奋斗多年,她在乎的只有事业和成绩,好像对于婚姻都不怎么执着,结婚离婚,甜的苦的,她像冷脸穿过两扇门。
无论是交往过的男人还是结过婚的孙承达,她也都能迅速抽离。
父亲、母亲和蒋山川的故事让她看到一种可能性,原来人可以这样不顾自身安危去帮助和扶持别人。
对母亲而言,蒋山川那破旧的三居室也一定比空荡荡的三层楼房要温暖。
相比之下,她觉得她缺少了很多东西,她第一次觉得遗憾。
“你们想结婚就结吧,我不阻拦了。”
她还想说“我只是心疼你”,可她还是没有说出口。
“结不结的,都无所谓,现在这个年代,也不会有人指指点点。”母亲回头看她,道,“你也别觉得我委屈,蒋叔叔虽然没有钱,可他待我很好,比你爸以前还要好。
“小刚也不错,别看他块头那么大,可是心里还是个孩子。那天就是因为蒋叔叔搬快递时撞到了我,他想护着我,可他趁不住手上的劲儿,一下子就把他爸连人带箱子推了下去。老年人骨头脆,一下子就骨折了。”
母亲叹了口气,道:“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也不是吃得好穿得好才算好,心里舒服才是真的好。”
“你觉得好就行。我给你的钱,你拿去给人还吧,我把上海的房子卖了,现在手上也不缺钱。”
“怎么突然卖房子了?好不容易买的。”
“我跟孙承达离婚了。”
江水平静地流动,母亲盯着冯自珍看了很久。
“这才几年呀?”
“不到两年。”
“怎么了呀?”母亲惊讶无措的样子像个孩子。
“过不到一起了,人家喜欢别人了。”
冯自珍怎么也没想到,她的随口敷衍竟然让母亲掉下了眼泪。
“怎么这个样子?”她有些激动,“我找他去,我问问他。”
冯自珍一阵苦劝,才让母亲平静下来。
两人在江边站着,吹着细风,看着宽阔的江面。
“我文化水平低,你什么都不跟我说。”母亲道,“有时候看看别人家的母女,亲亲热热的,也羡慕。”
“不是你文化水平低,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冯自珍道,“我以前太骄傲了,我从来没有尊重过你,总以为自己什么时候都是对的,直到这次离婚。
“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但我的骄傲全被击碎了。也许,生活根本没有明确的对错,好好生活才是唯一的路。”
“唉,你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听不懂也没关系,你高兴就行了。”
冯自珍搂过母亲的肩膀,动作有些生疏,却觉得温暖,“以后每周都给我打个电话吧,有什么事儿别再瞒着我了。”
母亲狠狠地点头,眼角有泪花闪了出来。
(《母亲的选择》九锡/著 完)
主播:瑶光/江大桥
编辑:阿菁
往期荐读
“因为爱你,所以打你”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每天读点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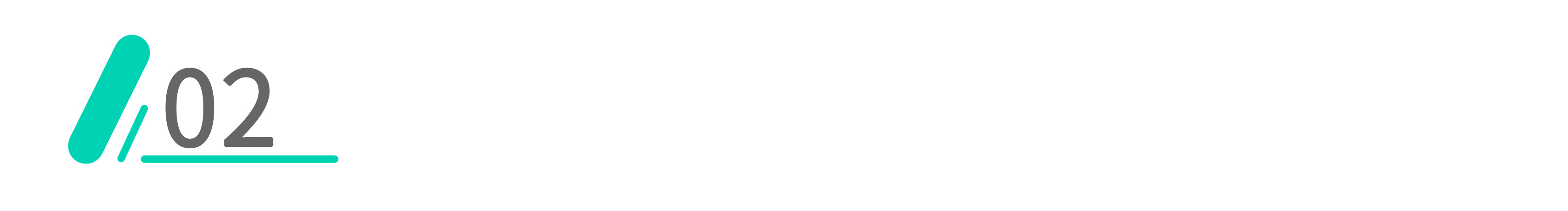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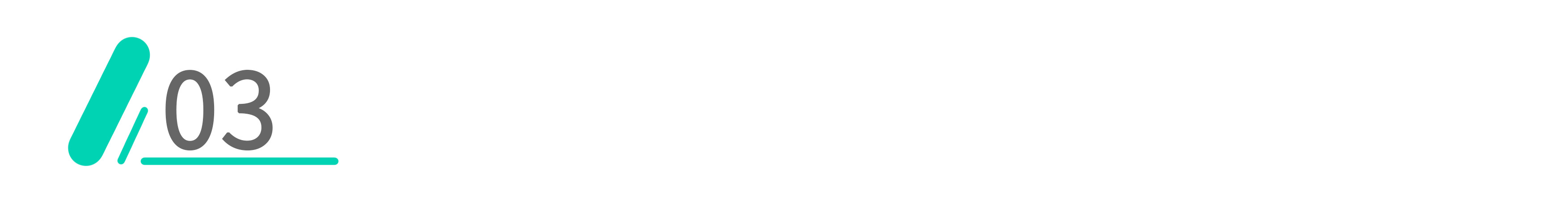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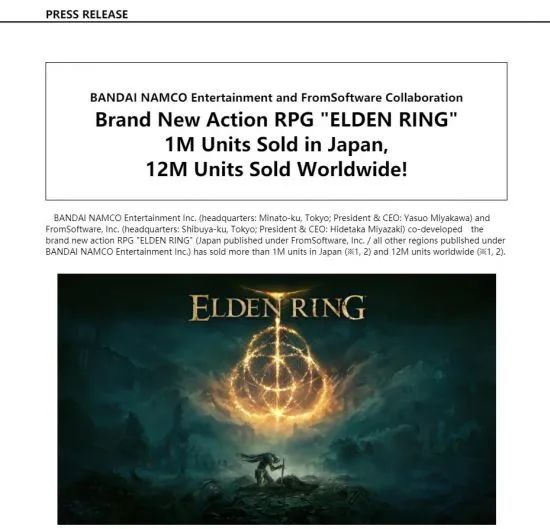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