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不高雅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米兰·昆德拉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俘虏,与一群(同样被俘虏的)英国军官囚禁在一起,他们常常因为雅科夫的大便把厕所弄脏而指责他。终于有一天,雅科夫因为不堪他们的指责和辱骂,投向了营地的电网,自杀身亡。
雅科夫既是“上帝之子”,又被上帝打入地狱,人类历史上最具强权人物的儿子,为了微不足道的粪便而死,截然相反的事物竟然能互相转换,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状态之间的距离竟如此狭小。
弗兰茨为了“伟大的进军”而死,昆德拉却评论说,斯大林儿子的死才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学之死”。
我曾经在一篇日记的评论里说,贝多芬生活习惯非常的邋遢,用来作曲的房间里堆满了垃圾,马桶就放在他所使用的钢琴后面。
后来有一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已经微醺的他非常认真地给我说,他不能忍受我把他所崇敬的贝多芬和排泄物联系在一起,如此这般的“不尊重”。
“粪便是比罪恶还尖锐的一个神学问题”,诺斯替派教徒断言基督“吃,喝,就是不排泄”。以此类推,乐圣家是否也完全可以排除清洗马桶的困扰呢?
雅科夫的死为何比弗兰茨的更“杰出”,是因为目的崇高的伟大进军成为了一种扭捏作态的媚俗表演,轻与重在瞬间发生了逆转。而很多时候,古典音乐,以及古典音乐的听众,正是在做着这样一场“伟大的进军”。
古典音乐是否比其他的音乐类型更高雅?恐怕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的。我认为,同样是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愉悦,古典与摇滚并没有质的区别。
古典音乐可以称为“严肃音乐”,而不能称为“高雅音乐”,“阳春白雪”的结果是“和者寡”,古典音乐在完成自我神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许多的潜在听众。一味强调古典乐的高贵出身,难逃弗兰茨式的媚俗之死。
西方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萨特认为“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听众需要正确的引导,如果一开始就认为古典音乐端着架子,面目冰冷,那进一步的欣赏就更加困难。在聆听古典乐者日益稀少的今天,“高雅音乐论”可以休矣。
让马桶在贝多芬家的钢琴后面安然沉睡吧。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美在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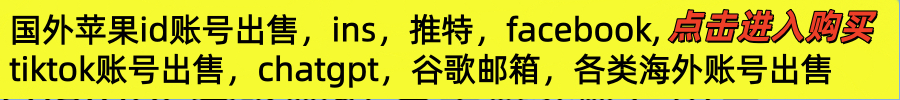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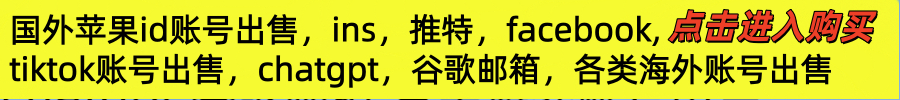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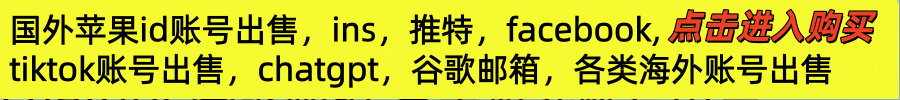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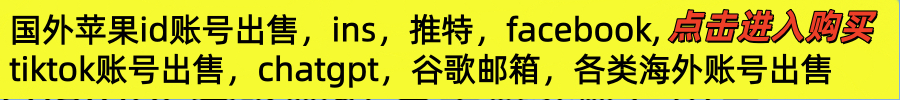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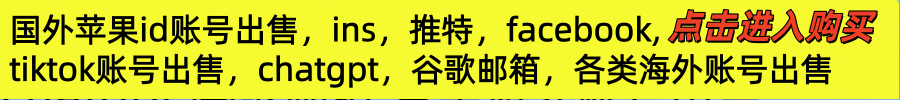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
黑公网安备 23010302001359号